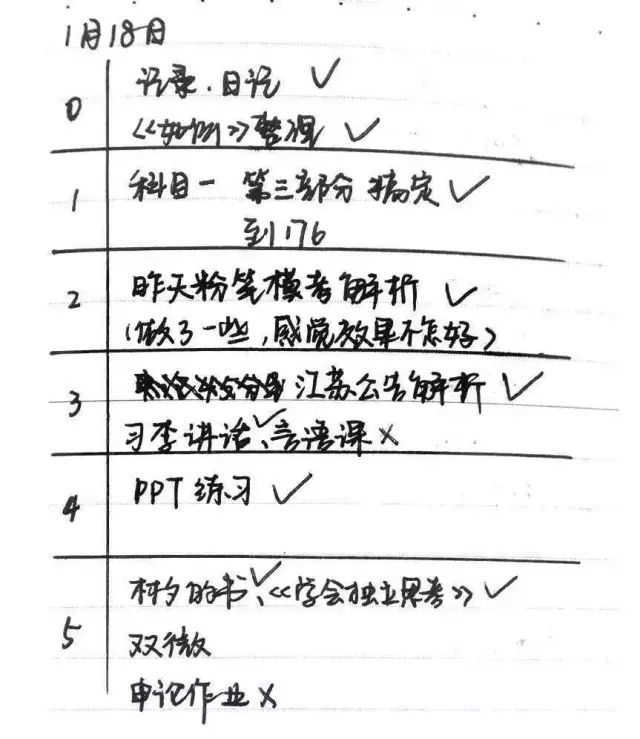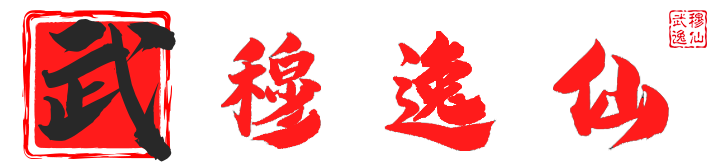上海市区淮海路上一大早便热闹非凡。那琳琅满目的商品,令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陈江河在人群中钻来钻去,在百货商店,陈江河驻足在袜子柜台前,微笑地扫视了一圈各种款式的袜子,慢慢地,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
“同志,你把那几双袜子都拿给我看看。”
售货员递过袜子:“天赐,国际大品牌!质量信得过。”
陈江河皱着眉说:“这上面明明是玉珠牌袜子,怎么全放在天赐袜业的柜台里了?”
“天赐和玉珠是同一家工厂生产的。”
“谁跟你说是一家的?”陈江河怒指柜台,“我强烈要求你把这些袜子撤下来,玉珠牌是我们的袜子!”
陈江河开着车,旁边老严唉声叹气:“江河,根据几个商场回馈的消息,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。上海、杭州很多地方都把我们玉珠牌袜子归为杨氏天赐袜业的子品牌了。”
车刚进厂就听到隆隆的推土机声,陈江河探头出去:“怎么回事?”
“厂长,我们按您的指示正在拓展厂区呢,新的生产线已经到了!”小蒋快跑上前兴奋地说。
陈江河脸色大变,跳下车快步往老厂房走去:“谁让你们干的,快停下来!”
“杨厂长说是你们商量好了的。”小蒋诧异地看看老严。
一辆推土机正在推倒老厂房的最后一堵墙,陈江河面对着废墟停住了脚步,眼睁睁看着那墙轰塌了。陈江河脸色痛苦、难受,随后踩上了还冒着烟灰的残砖破瓦上,俯下身焦急地寻找着。
“厂长小心!”
陈江河歇斯底里地翻着一块块砖头,执着地在废墟中翻找……杨雪站在远处,抱着胳膊静静地观望陈江河。陈江河铁青着脸走到杨雪面前,声音都有些嘶哑:“为什么要这样做?”
杨雪无辜地苦笑:“新生产线都进来了,没地安放。”
陈江河愤怒地当众吼起:“你经过我允许了吗?!这个袜厂不是你的天赐袜业,我宁可不要新生产线!”
工人们聚拢在四周,惊诧地望着发狂的厂长。
“陈厂长,旧的不去新的不来,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不懂吗?企业要发展,不能老抱着回忆吃饭。”杨雪脸色难堪地说。
陈江河一挥胳膊:“你少给我讲大道理!”
小蒋想上前劝解,被老严偷偷拽住。
“争风吃醋呐,你小子懂不懂啊!”
杨雪沉默了一会,昂首转身扬长而去。
陈江河悠然自得地在车间巡视,时而和工人说着什么,时而拿起袜子看了又看。老严愁眉苦脸地站在一旁,见陈江河无动于衷,干脆将他拉到一旁:“杨厂长走了三天连音信都没有,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?”
陈江河专注地看着袜子:“天塌不下来,就算杨氏全面撤资,大不了我们回到起点。”
“厂长,快去接电话,局里来的!”陈江河一愣,匆匆跑进办公室拿起电话:“喂?我是陈江河。”
电话里传来局领导的声音“小陈,你面子大啊!杨氏集团的杨总大驾光临了,点名要见你。”
陈江河愣了一下,为难地说:“王局,我这忙着抓生产呢,哪挤得出时间?”
“别废话,这是政治任务!现在全市上下都忙着招商引资,这可是大上海来的大财神,别人想见还见不到呢!”电话那头挂上,陈江河有些哭笑不得。
陈江河走出电梯寻找着杨天赐住的门号,开门的是杨雪,只见她两眼通红像是刚哭过。陈江河怔怔地打量,刚想招呼,杨雪低头侧身让过。一个白发老者笑容可掬地打量着自己,原地未动伸出手来:“陈江河,大气,你这名字我听了不下百遍,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哟。”
陈江河忙上前双手握住:“杨先生,您好!您是我国商界传奇,我们晚辈见您才不容易。”
杨天赐朗声笑起,转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女儿。杨雪走出房间随手带上了门。陈江河有些诧异,杨天赐坐在沙发上招呼了陈江河一声:“随便坐。”
“祖上哪里人?家里是经商的吗?”杨天赐气势不凡。
陈江河恭敬地回答说:“我是个孤儿,一个亲人都没有。”
杨天赐细细打量:“不容易呀,江河,你能走到今天,想必有过人之处。之前我很好奇,能跟杨氏百货争抢市场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,有什么背景。老实说,三年前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,今天我有点后悔了。”
陈江河尴尬地笑笑:“杨先生,感谢您当初的……”
“不过很快我就释然,英雄必是横空出世!且不问出处,更何况少年英雄即将为我所用。”
“杨先生,我从小听着英雄的故事长大,我崇拜英雄,渴望当英雄,可是我不是。我只不过是义乌乡下的填栏猪,饿不死,能吃苦,敢拼一把。我哪里配得上您那个‘英雄’称呼啊?”
“你非常聪明又刻苦用功,是一直与时间抢跑的人,你应该成为创业路上踏平坎坷的一个商战英雄。”陈江河迟疑了一下,刚要答话,杨天赐起身背手走到落地窗前,“三天后你将被任命为杨氏集团总裁助理,一个月内我将追加一笔投资到袜厂,全面打造袜业生产基地。一年后你将升任副总裁,辅佐杨雪接手杨氏百货。”
“杨先生您说什么,我……”陈江河瞠目结舌慢慢起身,完全被杨天赐的话打蒙。
“江河,我把我唯一的宝贝女儿托付给你,女儿是父亲的命根子啊!你懂吗?请你帮我和我女儿一块走下去吧,你决不能辜负我的宝贝,我的命根子啊!”杨天赐不容打断地回身,深情地注视着陈江河,面容越看越慈祥。
陈江河被噎在那。
车在路上疾驶。杨雪望着车窗外沉默不语,陈江河有些尴尬,暗中偷偷打量着美丽的倩影。杨雪突然轻声说:“这三天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三天,我刚知道我爸爸得了癌症,医生会诊,说只有一年的时间了。”
陈江河目光一紧。
杨雪握住陈江河的手:“在一切安排就位之前,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,你要帮我。”
陈江河瞥了眼开车的老司机。
“他是跟了我爸多年的吴叔,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”
陈江河百感交集,长叹一声:“真想不到会发生这么多事,你爸说投一笔巨资建生产基地是什么意思?”
“这点用不着你操心了,我爸已经和市领导沟通了,双赢的局面,杭州袜厂将成为我们杨氏集团最大的天赐袜业生产基地,而且会解决本地几千人的就业问题。”
“那玉珠牌袜子……”陈江河皱着眉问。
“都将成为历史,包括政府安插人事,无孔不入的裙带关系,还包括你的回忆。”杨雪哀怨的目光注视陈江河,陈江河躲避不开,转头默默地望向窗外,“我爸爸觉得很奇怪:我从小是个坐不住的人,不能专心干一件事情,现在怎么会扎在一个小小的袜厂,刮风下雨,不以为劳,露宿夜行,不以为苦。连续关心产品营销、市场推广几个月?现在他明白了,因为有你。”杨雪突然眼圈一红无声地抽泣,头慢慢地侧靠到陈江河的肩膀上。杨雪是水蜜桃型的大胸,偏偏还是高个细腰,平时走腻了扮嫩的穿衣风格,如今尝试着成熟从容的名媛造型,昨天玫瑰花朵图案的长袖连身裙穿起来非常高贵,那腰部褶皱的小心思让她充满自信。今天穿着泡泡长袖加娃娃领的高腰连身裙,令她瞬间变身为甜美女生,回头率超高。陈江河看了,心中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杨雪无意间在陈江河面前将头发挽起,露出了一款精致的珍珠项链,让她显得又娇嫩又贵气。杨雪是一个开心的好伙伴,对新生事物充满热情。
陈江河屏住呼吸目视前方,不敢再看香气袭人的杨雪。
“我现在才明白你离开义乌的真正原因,骆玉珠。这么多年你心里一直有这个女人。你也是为了她才守住这个袜厂的,对吗?你还用她的名字命名袜子品牌。”
陈江河痛苦地说:“所以你推倒了那堵墙。”
“我要把你心里那堵墙推倒,你的心才会对我敞开。江河,你聪敏过人,才华横溢;你杀伐决断,深谋远虑。袜厂、我、杨氏集团都需要一个男主人!”杨雪含泪看向别处。
陈江河喃喃地说:“杨雪,再给我点时间。”
车疾驶而去。
月亮出海了,在腾空的一瞬间,它仿佛猛地一跳,浑身披满水花,把多情的天空冲洗得分外明丽和洁净。
愁眉不展的陈江河在昏暗的灯光下无助地拨通了邱英杰的电话。“厉害啊!从投入资金、机器开始,杨天赐就已经把你们当成了他天赐的生产基地。他根本没把玉珠这个品牌放在眼里,江河,我们还是太嫩了。”邱英杰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。
“现在全厂的工人包括上面领导都很激动,他们欢迎杨天赐的投资,除了我跟小蒋。”
邱英杰激动地说:“这就是商业资本的厉害!杨天赐的上一辈是红色资本家,他本人是咱们中国最早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。他走在最前列,眼光也比我们看得远。江河,我倒劝你接受这个任命,到最前沿去磨炼自己,要不了几年,杨氏集团也会在你的手里风生水起、纵横天下的!”
陈江河长长地叹了口气:“英杰哥,我忘不了初心!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留在袜厂?为了那堵墙。我现在心里空落落的,玉珠牌说没就没了。”
邱英杰那边的声音放缓:“兄弟,三年前哥已经帮你注册玉珠牌商标了,你要想保留,谁也抢不走。”
陈江河猛地站起身,眼睛发亮:“注册了?啥时候?我怎么不记得?”
邱英杰笑起:“我提醒你多少次,你都不当回事,那年我去杭州开会,专门把你叫到杭州商标局大厅签的字,还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呢,你这个大忙人忙着谈生意签完合同就跑了,当然不记得。”
“我的哥啊,玉珠牌有救了!哥,你才是真正的高人!”
“听你这意思,你心里还是不甘心哪,值得吗?”邱英杰叹息。
陈江河激动:“英杰哥,值得,有你这一手帮我留着,我就有跟杨天赐谈判的本钱!”
“你还是不想做驸马,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她,但人各有命,你也得有你自己的生活和未来。”
陈江河深吸一口气,声音颤抖着:“我想最后再见一次她,哪怕隔老远看一眼,我再放下……”
二
江南的雨,一丝一丝地飘落着,滋润着树木花草,为大地生物带来了一份希望,也为河塘的水鸭带来了一股愉悦的情趣。
陈江河撑着油纸伞,沿着石板路寻找着骆玉珠。
他的裤脚已经淋湿,只得疲惫地靠在屋檐下躲雨,望着空空荡荡没有行人的街道……陈江河真希望,千万不要与那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擦肩而过。
陈江河独自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寻觅,他多么希望,突然出现一道彩虹,天上的云彩把那个哀怨又彷徨的姑娘送到眼前啊!
雨过天晴,赵姐正在对面吆喝着摆在摊里的东西,这边商店里的人跟陈江河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,陈江河穿过马路:“大姐,跟您打听个人,您认识骆玉珠吗?就是那个带着一个六七岁男孩的女人。”
赵姐愣了愣,疑惑地反问:“你说的是天儿?”
陈江河呆住:“天儿?她在哪?”
“还没出摊呢,你是她什么人?”赵姐上下打量着陈江河。
陈江河含笑:“我们是义乌老乡。”
远远地骆玉珠背着两个大包裹,小王旭也提着一个小袋子跟随走来。
骆玉珠突然停住脚步,脸色大变,小王旭诧异地看着妈妈。骆玉珠拽着儿子转身就走。“妈,不卖了?”小王旭惊讶地问。
骆玉珠也不答话,苍白着脸一路匆匆前行。小王旭回头张望着对面那瘦高的身影,露出了好奇的目光。
“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真的不容易,每天起早贪黑地拉货卖货,谁看着不心疼?”赵姐叹息着。
陈江河苦笑着默默点头,眼巴巴地望着马路尽头,却没意识到身后消失的人影。
厨房内昏黄的灯光下,是骆玉珠那劳累不堪的身影。她正弯着腰,心事重重地切着菜,小王旭看着课本,偷瞥了一下状态不对的妈妈,骆玉珠切到了手,疼得忙含住手指。
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“就是这里,我帮她在这租的房,有我在,没人敢欺负她娘儿俩了!”赵姐敲着门叫喊着,“天儿!天儿!”
骆玉珠愣了一下,将门反锁。小王旭刚轻声叫了声“妈”,骆玉珠已经捂住儿子的嘴,摇头示意。
“哟,不在家,估计也没走远,要不您等会。”门外赵姐的声音。
“麻烦您了啊,谢谢。”
百感交集的骆玉珠,目光痴痴地望着门外那个模糊的轮廓。
陈江河站在门口,没有想到此时他要寻找的人却在屋里忐忑不安地躲着他。陈江河朝四周看了看,抬手又看看表,最终等不下去了,掏出钢笔在纸条上匆匆写下几句话,塞进了门缝。
脚步声远去,骆玉珠这才松开手,颓然坐下。
小王旭走到门口捡起地上的纸条。骆玉珠默默接过,一行清秀大气的字:玉珠,别再躲我了,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好苦。
“妈,你为什么要躲这个叔叔?”
骆玉珠低头,尽量不让儿子看到自己在哭泣,一串串泪水却不争气地滴落了下来。
小王旭目光复杂地凝视着母亲。骆玉珠突然起身,慌乱地收拾起东西:“走,我们走,去找新的家。”
小王旭吃惊地看着妈妈。
厂里的电话越催越急,陈江河还不死心,他又来到出租平房,一下下疯狂地砸着屋门,他的手掌已经破裂淌出血来了。
陈江河痛苦不堪,他的头重重地顶在门上闭眼喘息,周围的邻居都被剧烈的砸门声惊到,探头出来张望。
陈江河终于提着包,迈着沉重脚步走向了停靠着的列车,上车前他回身绝望地看了一眼才走进车厢。陈江河怅然若失地在窗口坐下,突然一激灵,对面列车上有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陈江河猛地站起身,脱口叫起:“玉珠!骆玉珠!”
骆玉珠身子一颤,从对面列车窗口转过身,陈江河用力拍打着窗户。
王旭吓得看着妈妈。骆玉珠还想拉着儿子往人群里躲,陈江河用力抬起窗户探头叫喊:“玉珠,你听我说一句!八年了!你就这么忍心?你起码要跟我说句话!”
列车悄然启动,两边车厢交错前行。
陈江河用尽力气探出头大喊一声:“你在下一站等我,一定等我!骆玉珠,这些年我没有抛弃过你,我一直在守着它……”
骆玉珠近乎绝望地冲他摇了摇头,嘴唇颤动说着什么。
陈江河突然从包中掏出一块砖头,双手高高举出窗外,隐约地可以看到两个小人和一行字。
骆玉珠转过头泣不成声,小王旭目光极其紧张,仰头看着母亲。
骆玉珠泪如雨下。
陈江河跳下出租车,慌乱地将钱塞给司机,大步跑上站台,喘息着朝站台四周观望。远处一列火车刚刚驶离,站台上没有他想见的人影。
陈江河痛苦地摇着头,一下子松懈下来,无力地转身。突然陈江河眼睛一亮,骆玉珠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,牵着儿子一动不动,她的眼神混杂着不安、期待、犹豫。陈江河的鼻子一酸,眼睛湿润了。
骆玉珠望着陈江河的眼神,突然变得坚定,灿烂地笑起,同时无声的泪淌落着……
陈江河肩背手提所有的行李,起劲地走在袜厂外的小路上,还不时地回头看看,骆玉珠报以温柔的凝视。骆玉珠拉着儿子蹒跚跟在后面,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王旭懵懂地扯扯妈妈的手:“妈,我们去哪儿?”
“叔叔去哪我们去哪。”骆玉珠轻声平静地说。
“我们不回家了?”
骆玉珠一笑:“小旭,现在是回妈妈的家。”
陈江河没有回头,眼中闪动着晶莹,毫不疲倦地起劲走着……
三
鞭炮噼里啪啦炸响着,迎宾喜庆乐队起劲地吹打着。在“热烈欢迎杨氏集团投资考察”的横幅下,局领导领着杨天赐走进了工厂大门,杨雪面色阴沉地跟随在父亲身后。随行记者不时地拍着照。老严,小蒋急得不行,小声嘀咕:“厂长怎么还没回来?这不会……”
突然小蒋叫起:“厂长,厂长回来了!”
顿时喧闹声变成了鸦雀无声。陈江河领着骆玉珠母子俩一路走来。局领导叹息摇头:“这个陈江河,干吗去了!他身后那个女人是谁啊?”
杨雪回头望去,突然目光一沉,脸色死灰一样难看。
骆玉珠抬眼扫视,目光准确地落在高个子美女杨雪身上,两个美丽的女子异样地看着对方。骆玉珠嘴角泛起一丝微笑,杨雪睫毛颤动转望别处。杨天赐意味深长地瞥了眼女儿,若有所思。
陈江河将母子俩领进宿舍,忙不迭地从老严手里接过两个饭盒递给骆玉珠。“食堂留的饭,已经凉了,那里有炉子你热热再吃。”
“快点吧厂长,你得赶紧去陪着贵客!”老严在门口催着。
陈江河抚摸着王旭的头,王旭胆怯地往妈妈身后躲去。骆玉珠搂过儿子:“江河,先忙你的,别让人家着急。”
陈江河被老严拽出门,回头嘱咐:“玉珠,你们先好好歇歇,床上那被子是干净的,壶里有热水……”
骆玉珠眼中充满温润,冲老严:“您快把他拉走,真絮叨。”
老严忙笑着点头,强拉陈江河下楼梯,骆玉珠上前将宿舍门关上。
窗外传来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声还伴着掌声。
骆玉珠又将窗户关严,转身扫视屋内环境,朝儿子释然一笑。
陈江河被拽到台上,掌声中杨天赐起身与局领导握手微笑示意,记者围着拍照。杨天赐瞥见后台的陈江河,迟疑了一下悄然走来。
台上领导激动地说:“我们棉纺总厂经历了痛苦的转型时期,尤其是曙光袜厂,年生产总值由 1986 年的五十万飞跃到今天的七百万,这与同志们的奉献和努力是分不开的……”
陈江河扶住杨天赐:“杨总,我有个决定想跟您好好谈谈。”
杨天赐仿佛已经明白了什么,意味深长地打量。陈江河转身带路,两人向外面走去。
陈江河倒好茶水,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,杨天赐默默审视。
“通过这几个月打交道,我深信杨雪是非常优秀的管理人才,您有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儿真值得骄傲,把杨氏公司交给她没问题。您老踏实养病,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
杨天赐没有回应,冷笑地看着陈江河。陈江河不停地擦着汗说:“我是个粗人,您也许听杨雪说过,我连爹妈是谁都不知道,命贱得就像鸡毛一样,跟您这种大家族没法门当户对。”
杨天赐缓慢地起身说:“如果我没听错,你是想对我那天的托付说不。”
陈江河双手作揖,谦卑地笑着:“杨先生,那天您许诺我的太多了,真把我吓着了,我怎么受得起,更不敢辜负您的女儿。”
“为什么你要拒绝?”杨天赐百思不得其解。
陈江河一脸苦恼:“我觉得不般配。自己也没那能力,我陈江河憋足劲也就管个百八十号人,一听说要做大事,这些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,您说天大的好事砸下来,要强加给一个没能力扛的人,这不是害他吗?”
杨天赐凝视许久:“是因为你今天带回的那个女人?”杨天赐背着手在屋中徘徊。
陈江河无语,他的目光也紧张地跟随着他的身影徘徊。
窗外传来热烈的掌声,杨天赐背手而立:“不是一家人那就只能说两家话了,没有你,我凭什么要往这里注入那么多资金和设备?”
“杨总,您这都是客套话,其实我明白,就算没我地球照转。您需要的是这里的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;从你们一开始投入,您就没想扶持玉珠品牌,不过为你自己的华丽特袜业寻找生产基地,顺便把跟您抢市场的玉珠牌灭掉。这种一箭双雕的好事怎么会因为我而放弃呢?”陈江河依然不卑不亢地微笑着。
“你就不心疼你的玉珠牌吗?”杨天赐吃惊地转身,重新审视陈江河。
陈江河一拍脑袋:“瞧我这记性!我特意给您带来了复印件。”陈江河转身从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资料,双手放到杨天赐面前,“这是三年前在杭州商标局注册成功的玉珠牌袜子,申请人陈江河。我这次去杭州咨询了一下,这个品牌在承包期间归袜厂和我共有,承包结束玉珠牌就完全是我的了。”陈江河坐在一旁微笑。
杨天赐皱眉翻看着注册资料:“三年前你就想到这步棋了?”
陈江河憨憨一笑,“我哪有您那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本事,你下一步棋得想三步,我只能盯着眼面前,搂草打兔子—歪打正着!”
“毕竟你还是失去了很多,因为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,你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么多,堂堂男子汉,应该胸怀全天下,你想过代价吗?值得吗?”杨天赐注视着陈江河。
“想过。”陈江河收起笑,迟疑了一下抬起头,“因为她再也伤不起,因为我答应过,一生一世不抛弃她。”
骆玉珠一边在炉子上热饭,一边逗床上躺着的儿子,王旭昏昏欲睡睁不开眼:“小旭,吃点再睡,马上就热好了。”
有人敲门,骆玉珠将饭盒挪开,手被烫了一下,连忙用嘴吹着手指走过去开门。
高雅端庄的杨雪经过精心装扮,更是一副白领丽人的俏模样,她身着西服裙,披着一头波浪卷发高傲地站在门外。
骆玉珠愣了一下,笑着压低声:“孩子睡着了,您有事吗?”
杨雪看了眼床上的孩子:“去我屋里谈谈。”
骆玉珠点点头,杨雪走向自己的房间。
骆玉珠关好房门,转身慌乱地在包裹里翻找起衣服,又在货物中挑着首饰,对着镜子一件件地试。
骆玉珠越穿戴越烦躁,突然看着镜中的自己噗嗤一笑,将衣服和首饰抛在桌上只是理了理头发,转头看看熟睡的儿子走向门口。
杨雪将骆玉珠迎进屋内。骆玉珠攥着一个凉酒糟馒头大方地走进去。杨雪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,直到她转身坐下,才慢慢地将房门关上。
“你是骆玉珠?”杨雪轻声问道。
骆玉珠笑着点头:“能给我来杯热水吗?这馒头有点凉,饿死我了。”骆玉珠掰下一小块馒头塞进嘴里,边嚼边扫视屋内环境,“您这屋一看就是讲究,跟您比起来江河那屋就是猪圈,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杨雪将水端到她面前,在对面坐下看着她吃。
骆玉珠递上馒头:“您来点?”
“骆玉珠你配不上陈江河。说实话,见了你我有点失望,我原以为让他想了八年的女人,该怎么出色就怎么出色,哪知道……”杨雪纹丝没动,冷冷的。
骆玉珠艰难地咽下,忙端起水杯喝了一口说:“你挺会埋汰人的啊!”
“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”
骆玉珠掰着馒头闻闻香气:“这馒头让我想起十几年前,我跟他住在桥洞里的时候,我熬糖让他挑出去换,有时候带回这么块酒糟馒头来,我俩就跟过节一样。陈江河挺会烤馒头的,那香味我现在还记得。”骆玉珠似乎无视杨雪的存在,眯起眼看着馒头甜甜地回忆着。
杨雪难抑激动,连声音都颤抖着:“你跟别人成家了,还生了孩子,而他一直单身。骆玉珠,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。”
骆玉珠淡然一笑,又扯块馒头塞进嘴里咀嚼:“八年前,有人说过同样的话,你不能这么自私,你会耽误他前程。那时候我真傻,之后我躲了他八年,你数数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八年,就因为别人的一句话……你们厂的酒糟馒头真甜!来一块吧?”骆玉珠扯下一片递上。
“你知道我能给他带来什么?对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远大前程,是高高在上的地位!我都能给他。在你没来之前他已经接受了。”
“对他来说什么最重要,只有他自己最清楚,就像这酒糟馒头,我吃着又香又甜,你却不屑一顾,因为你没有一起逃难挨饿的经历,因为你没有跟他分吃过一个馒头。”
骆玉珠举着小半块馒头声情并茂地给杨雪讲述,杨雪脸色苍白抱臂听着。骆玉珠拿起水杯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,自己沉浸在回忆里乐得不行。“还有这袜厂,我俩为了提货骗人家,说是厂长的二姑和二姑夫,那人都傻了!后来发现厂长是一老头!我们赶紧逃跑了。”
骆玉珠捧腹大笑,笑出了眼泪,完全无视杨雪的存在。
杨雪深吸一口气,憋出一句:“你笑够了吗?”
骆玉珠吃尽最后一块酒糟馒头,将水饮尽一抹嘴起身:“谢谢你的热水。”
“还有话吗?没有的话我给江河洗衣服去了,刚才我看他屋里臭烘烘的,一盆衣服估计一礼拜也没动。”骆玉珠摇头叹息,“你说这厂里那么多的女人,也没一个人帮厂长洗洗。”
杨雪目光呆滞,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。
“那墙是我推的,他守了那么多年,最后还是一片废墟。”骆玉珠走到门口,身后传来杨雪的冷笑。
“你推的呀,谢谢啊!我要是没有看到他举起的那块砖头,还真是没有勇气回来!”
“他找到那块砖头了?”杨雪崩溃地闭上眼睛。
“要不说他傻呢,一块砖头一直背着,你说人都找到了,那墙还算什么呀!您踏实坐着,我洗衣服去了。”
豪车在公路上疾驶,杨氏父女并肩坐在后排,神色各异。
“爸,撤离资金和设备,我要不惜代价灭掉玉珠牌,我要让陈江河几年的心血白费!我要他知道放弃的代价!”杨雪恨恨地说。
“我已经答应陈江河带着玉珠品牌离开,很多事情他想到了我们前面。这个人不简单哪!”杨雪吃惊地看着父亲。
杨天赐握住女儿的手:“早在三年前,他就已经注册了商标,我投入资金设备到这个袜厂,所有的战略意图,陈江河都一清二楚,他知道这个生产基地对杨氏天赐袜业的意义,更知道我不会轻易放弃。倒是你小雪,有点让爸爸失望。”
杨雪含泪看着父亲。
杨天赐一字一顿:“记住,行商之人永远不可意气用事!不能显露人性的弱点。暴露了,你成了赤膊上阵的许褚,也就败定了。”
副驾驶位上的助手听着大哥大,转身:“杨总,我们的人查清楚了,陈江河在玉珠牌的基础上又加注了银珠、金珠系列。”
杨天赐目光一沉:“商品涵盖是什么?”
“涵盖很多,涉及百货、五金、首饰,几乎与我们重合。”
杨天赐将女儿的手重重地一握,语重心长:“爸爸总有走的那一天,将来你务必要小心这个对手。”
豪车在国道上疾驶而去。
四
一片枫叶无奈地飘落,微风拂过,老严和小蒋带领员工围拢在陈江河身边依依不舍,陈江河与每个送行的人握手告别。
邱英杰的车已经停在厂门口,他领着邱岩上前。
“邱大哥!”
邱英杰接过行李边装边打量:“玉珠,这是你儿子?告诉叔叔叫什么?”
王旭躲到母亲身后。
“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没出息!哟,这是你闺女啊!”
骆玉珠说着,眼睛一亮拉过羞涩的大眼睛邱岩,目光停在她脖子上的古玉挂坠上。
“江河给她的,快给阿姨摘下来。”
骆玉珠按住:“别摘,孩子戴着挺合适。”
邱英杰感慨地望着人群:“玉珠,江河可是为了你净身出厂啊。”
骆玉珠也转头看了看笑着说:“算他聪明,现在他失去的,我都会帮他赚回来。”
邱英杰目光一凛,欣赏地打量骆玉珠。
“厂长,能不能不走?大伙还想跟你干呢!”
“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这个厂马上就要扩建三倍,还会有大批的新员工招进来,我已经跟局里请示,聘你和老严分任生产和销售的副厂长。”陈江河冷眼看着刚刚换上的天赐袜业豪华招牌,微笑着说。
老严百感交集地说:“我们苦了那么多年,总算熬到乌鸦变凤凰了,你却要走了。”
陈江河苦笑:“变凤凰了吗?也许从规模从待遇上是这样,可我们自己的品牌没了。老严,也许再过几年大家都富裕了,你才会发现最珍贵的是什么。”
老严无言以对,沉重地点头。
陈江河退后几步挥手告别:“大伙就送到这吧,接我的车来了,到义乌来玩,咱们后会有期!”
邱英杰开着车,瞥了后视镜一眼笑着问:“玉珠,在外这几年想不想义乌?”
“邱大哥,我已经八年没回去了,义乌是什么样子,我都忘了。”
“你绝对认不出来了!别说你,江河回去都得大吃一惊,现在义乌准备开放第四代小商品市场,所有的摊位都将搬进大楼里,你等着看吧,义乌将来的变化,会让你们瞠目结舌!”
“在楼里卖东西?那不跟上海的大商场一样了?”
邱英杰笑着说:“你们有点想象力好不好,别什么都跟传统的商场比,好像只有你一人去过上海似的,我们都是土包子!还有陈金水的变化你们也想不到。”
陈江河饶有兴趣:“我金水叔现在忙什么呢?”
“你们谁也想不到。全村的人都出去做生意了,唯独他心气全无,别人忙着赚大钱,兴什么,卖什么,他倒活得像老神仙一样啊!自己办了个养鸡场,羽毛加工厂。他说以前鸡毛换糖做梦都想换些鸡毛回来,现在干脆自己养鸡,做点鸡毛掸子毽子,让巧姑放在摊位上卖。”
陈江河与骆玉珠交换个眼神,疑惑不解的神色。
“陈大光也回来了,这小子不知在哪发了笔横财,闹着要跟巧姑补办一场婚礼。要说这是好事,可陈金水死活不让,也不拿女婿给的一分钱。”
邱英杰话锋一转笑着说:“哎,你俩要不要凑凑热闹也补办一个婚礼?”陈江河转头看骆玉珠,骆玉珠哭笑不得白了他一眼,又低头偷偷瞥了儿子一眼。
邱岩将冰糖葫芦放到玉珠身后的车枕上,玉珠装作没看见。王旭跟做贼一样,悄悄地伸出手,从后面一把拿过冰糖葫芦,藏在袖中。
邱岩露出了得意的笑,玉珠转头跟邱岩默契地眨了下眼。
邱英杰说:“当年篁园村玉珠那个小院环境好,就在新市场边上。江河非要再盘下来,就是多少年过去,花园似的地方寸土寸金,价钱有点贵。”
陈江河笑:“多贵也要租过来!人从哪走的就得回哪去。”
邱英杰朗声笑起,将一盘录音带塞进车载卡带机中,歌声传出。
“莫说青山多障碍,风也急风也劲,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……”
陈江河转头看着骆玉珠,也摇头晃脑地跟随唱着:“万水千山总是情,聚散也有天注定。不怨天不怨命,但求有山水共作证……”
骆玉珠没有笑,手轻轻攥紧儿子,伤感地看向窗外。
陈江河边唱边诧异地打量,似乎感觉到了什么。
车疾驶而去。
还是当年骆玉珠租的小院子里。
明亮的月亮,把大地照得一片雪青,房屋树木,都像镀上一层水银。院子一边栽着银杏树、水杉、罗汉松,另一边是小池塘,上面是鹅卵石砌成的阴阳鱼。大地上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雅致,那么幽静。清柔的银色透过窗子,映照在王旭熟睡的脸上,映照在王大山的遗照上。
骆玉珠深情地端详着丈夫遗像:“大山,让你看看这个小院,这是我遇见你之前生活过的地方。”骆玉珠抱着遗像,起身在屋里转了一圈,轻声商量般,“跟你商量个事啊。我还是回来了,带着咱儿子小旭。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,我现在给你讲。外面坐的那个男人叫陈江河,我十几岁差一点被我后妈卖给人贩子,后来流浪遇到了他,我们一起鸡毛换糖,一起过苦日子。后来镇长逼他娶自己的女儿把我俩打散了,我以为他对不起我,像我爸一样把我当废物扔掉,谁想到八年过去,他一直在等我,找我……”
陈江河一动不动坐在台阶上望着月亮。骆玉珠走出门静静地并肩坐下。陈江河脱下自己外衣给她披上。骆玉珠轻声地说:“跟做梦一样,就好像八年前的我们,一直坐在这里,只有指针转了一圈而已,什么都没发生。”
“怎么可能,一切都变了,你名字都改了。”
“天儿,你喜欢这个名字吗?以后没人的时候你就这样叫我,好不好?”骆玉珠嘴角泛出一丝笑意。
陈江河刮了一下她鼻子:“鸡毛飞上天,反正我是飞不出你的手掌心了。哎,有年春节下着大雪我赶到那,看见小屋里你们……”
骆玉珠捂住他的嘴,陈江河愣住,怔怔地瞧她。
“今晚什么都别说,就算这是一场梦,你让我做完它。”
两个有情人相依相偎在皎洁的月光下,谁都没有注意,王旭已经悄然爬起,稚嫩的目光中透着不解和仇恨……
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成为合法夫妻,恭喜你们。”办事员郑重地将小红本递到两人手上。
陈江河与骆玉珠都神色肃穆。邱英杰在相机后招呼:“你俩靠近点。陈江河,会不会笑?”
陈江河与骆玉珠的头靠拢在一起,并肩露出笑意。
“喜宴不摆了,但是酒我们还得喝。怎么样,晚上我办一桌?”邱英杰说。
骆玉珠面露难色瞥了眼陈江河。
“英杰哥,还是省了吧。我们不想让小旭知道。”陈江河笑着说。
“噢,那就你们俩偷着乐吧。”
骆玉珠含羞地说道:“邱大哥,瞧你说的,往后我们一定把喜酒给你补上。”
邱英杰大笑:“当然了,我可是你们俩的证婚人,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我。”
两个患难之交依然一前一后地走着,邱英杰充满诗情画意地展望着:“我看到了沉默了两千二百年的义乌,土地袒露出了血性的胸膛:那是包容所有人的胸怀,就像母亲庇佑着她们的儿女,大树遮蔽着脚下的土地一样。江河,我们生逢其时,我们并肩战斗吧!”
骆玉珠默默望着陈江河的背影。陈江河回头看她,伸出手来。
“人家看见了。”
陈江河笑了:“怕什么,我们已经是夫妻了,法律都保护我们。”
骆玉珠迟疑,陈江河的手已经拉住她,两人并肩前行,相视而笑。
院里院外热闹非凡,前来探望的陈家村乡亲几乎踏破了门槛。陈江河忙着应付,骆玉珠拉着冯大姐等人的手大声说笑,王旭也不自在地被人围着。
“鸡毛啊,想死我们了!这么多年,你也不回来看看!”
“叔婶,我这不回来了。”陈江河笑着说。
“鸡毛!为赶回来见你,我儿子大奔的轮胎都快磨平了!”一辆豪车停在院门口,大光爹还没进院就开始嚷嚷。
屋里人都一撇嘴。陈江河哭笑不得迎出院:“叔,您来了。”
大光爹脖子上挂着粗粗的金链,手上晃动着金戒指,热情洋溢地抱着陈江河拍打。
“哎呦叔,你身上这堆黄绳子把我眼睛晃花了。”
陈大光将车停好,晃悠着摘下墨镜走进院门,操着一口蹩脚的香港话熊抱过来:“鸡毛锅,兄弟我好挂住你吖!”
陈江河吃惊地打量着陈大光,没等他反应过来,屋里骆玉珠等人已经大笑起来。骆玉珠笑出眼泪说:“陈家村太厉害了,都出港商了!”
屋里冯大姐无奈地冲骆玉珠摇头。
外面大人们还在说笑,王旭悄然走进屋将门关上,谁也没有留意到他。王旭蹲到床头柜前轻轻打开抽屉,看到那个小红本,翻开一看是妈妈和陈江河的结婚照。王旭目光愤怒,想撕又不敢撕。
五
巧姑用力拍着养鸡场的门,陈江河提着烟酒和点心恭敬地站在身后。
“爸,鸡毛哥回来看你了。爸,你开门啊!”院里没有动静。巧姑一脸为难,回身轻声说:“哥,别说你,我爸现在连我都不见,天天就知道做毽子踢毽子,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瘾。”
“别勉强,巧姑,你现在跟大光可享福了。不是说你俩还要补办婚礼吗?”
巧姑凄然一笑:“享什么福!他现在只有钱了。”巧姑长叹一声,“不离就是好事了,以后慢慢跟你说吧。鸡毛哥,我真替你跟玉珠姐高兴,你们能守到今天,才是最幸福的。”
陈江河百感交集地看着巧姑:“你先回去做饭,我在这转会。”
巧姑看了看院门,又把话咽回,转身离去。
陈江河提着烟酒和点心,围着院子绕起来,后来干脆一屁股坐下,靠着墙大声地说:“叔,鸡毛回来了,我知道您一直关照我,袜厂缺货的时候您还劝乡亲们别去添麻烦。叔,要论做买卖,您才是真正的高人,乡亲都忙着赚大钱,您怎么关门养起鸡来了?”
院里依然没有回应。
陈江河无声地叹息:“叔,我把给您老带的烟酒放门口啦,我走了!”
陈江河刚要离去,突然身后一声脆响,一个毽子腾空而起。
陈江河吃惊地停住脚步凝望,墙内毽子不时被踢上半空,鲜艳的鸡毛在空中分外刺眼。
陈江河眯起眼,目光追随着飞舞的毽子,会心一笑,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出来。
陈江河在远处突然喊起:“叔,您等着,鸡毛肯定飞上天!”
鸡毛毽子稳稳地落在苍老的陈金水手中,老人一动不动。
陈江河刚回到家门口,满脸焦急的骆玉珠就冲出来。陈江河吓了一跳:“怎么了?”
“小旭不见了!我出去送冯大姐回来就见不着他了!”
“也许出去玩了吧,你别慌。”
骆玉珠颤抖着声:“他爸的东西,遗像都没了!还有这个……”
骆玉珠递上结婚证,两人并肩微笑的照片已经被剪出口子。
陈江河脸色大变。

![【学习强国】[挑战答题]带选项完整题库(2020年4月20日更新)-武穆逸仙](https://www.iwmyx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timg-300x200.jpg)


![【学习强国】[新闻采编学习(记者证)]带选项完整题库(2019年11月1日更新)-武穆逸仙](https://www.iwmyx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77ed36f4b18679ce54d4cebda306117e-300x200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