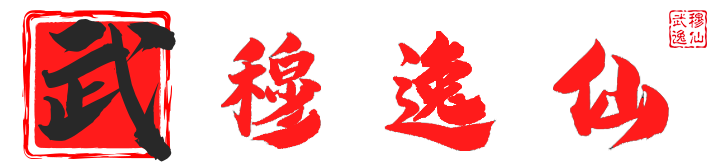在简陋的扳道工小屋里,骆玉珠睡得异常香甜。一直到第二天中午,她才被火车的轰鸣声惊醒了。她把小屋收拾干净,一出门就听见了远处传来的轰隆隆的响声。看到王大山也正扛着工具,从远处独自沿着轨道走回来。
一列火车开来,王大山爬上路基,站上高处举起小旗,火车鸣叫了一声开走了。
“大山哥,火车还向你打招呼呀—你还能指挥火车!太了不起了!谢谢你收留我,你好人有好报,我走了。”骆玉珠挥泪告别时,真想给大哥付一下饭钱,无奈囊中羞涩,只得红着个脸,口头表达感激之情。
“我只要按规章制度做事,就能完成任务!”王大山一本正经地说着,一动不动地望着骆玉珠渐渐地远去,直到骆玉珠的踪影消失了,才推开小屋的门。
简陋的小屋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王大山一眼就看到了叠放整齐的床上,昨晚被撕破的床单上,补上了一朵小花。王大山坐在床上,反复抚摸着那块补上的小花,心头涌上了一股莫名的伤感。
第二天,王大山巡完一天道,习惯成自然地站到了扳道工小屋门口,看着那两条静卧的铁路。临近天黑,王大山才走回屋里,一边喝着热水,一边啃着腌菜窝头。就在王大山吃得津津有味时,门被敲了个震天响,把王大山吓了一跳。他疑惑地起身打开门,王大山惊讶地大叫了声“你”。
站在门口的骆玉珠,满身脏兮兮的,头发也黏在前额,她疲惫不堪,怀着歉意笑着:“大山哥,我实在没地方可去了,只好回来找你,你昨晚睡觉的地方能租给我吗?”
王大山看了眼骆玉珠,她身后是一大堆用麻绳捆绑起来的垃圾废品。王大山突然关上门进去了,骆玉珠尴尬地站在门外,猫着腰收拾好垃圾废品,艰难地背在身上准备离去。谁知,王大山抱着自己的铺盖开门出来了,他闷闷地吐出一句话:“你就睡这里吧。”
“大山哥,我长期住在这里也不太方便,而且影响你巡道、对火车发号施令,我想去你住的地方看看,如果有合适的房子我租一间。
王大山又无奈地揺了摇头,苦笑了一声抱着铺盖走了。骆玉珠皱着眉,眼瞪着他,转身便关上了门。
清晨,骆玉珠推门出来眺望,王大山已经独自在铁轨上巡视路面了,远远的,两人对视着。
骆玉珠喊王大山过来,她指着桌上熬好的稀饭,揭开盖子,里面是两盘炒好的蔬菜还有窝头,王大山看傻了眼。
“中午你自己蒸饭,下米的时候水要高出一节手指头,这样蒸出的饭才不软不硬,记住了?”
骆玉珠想租个地方长期住下来,坚持去王大山住的地方看一看。王大山只得带骆玉珠来到一个草棚,将吱呀作响的栅栏门推开,里面全是稻草和杂物,铺盖就散乱地堆在上面。骆玉珠吃惊地看着,转头盯着王大山,心里非常感激这个闷葫芦。
王大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垂下头去。
二
陈江河手拿电话,大声地说着:“……这个女人,你必须帮我找,照片我给你寄了。湖南那边就拜托兄弟了,拜托了,兄弟!”
陈江河挂上电话,冲身后排队的人歉意地笑了笑:“对不起,我还得打七八个呢,你们去别的柜台看看吧。”
陈江河又拨通电话:“哥呀,我是陈江河……义乌的,原来卖暖壶的鸡毛!对对对,好久不见。我求您件事啊……”
打完电话,陈江河靠墙坐着,拿出洗印出的一沓照片,向柜台营业员借了把剪刀。剪刀比画在两人合影中间,迟疑了一下,他还是含着泪水一刀剪了下去。剪完照片,陈江河一一装进信封,用挂号信寄了出去。
从邮电局出来,忽然想起骆玉珠妈妈坟上的那双袜子,心头一亮,有了主意。
在杭州郊区的曙光综合厂大门口,陈江河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四周,生怕漏走了一丝希望。
一辆运货车驶出,陈江河忙起身追去:“师傅!师傅!”车戛然而止,陈江河扒着驾驶室的窗子,仰头问,“师傅,这两天骆玉珠来您厂进过货吗?”
司机诧异:“谁是骆玉珠?”
陈江河从袋子里拿出照片:“就是这个!”
“哦,她呀,很多天没来了。”听了司机师傅的话,陈江河失望地呆在那里。
陈江河没有死心,他相信玉珠迟早还要来厂里拿货,便继续蹲守在厂外,盯着大门直到天黑。
有一天,天刚蒙蒙亮,陈江河又往曙光综合厂大门口走去,边走边揉着迷糊的眼角。忽然,袜厂厂房里腾起一股浓烟,隐约有人喊叫:“快救火!快!”陈江河一惊,连忙跑进厂区。袜厂的原料车间里火势熊熊,值班看守厂房的是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,见了大火就手足无措。陈江河冲上前喊:“消防栓呢?水在哪?”
老人吓得面面相觑: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陈江河脱下衣服用力拍打,咬牙冲入火场,将几袋原料拖出大门,用废旧机器建成拦火墙,尔后接过别人递上来的消防水枪,重新冲入火中,不顾一切地灭火。由于拦火墙的阻隔,火势没有蔓延到成品仓库,不多时,原料车间的火就被扑灭了。
郑厂长急匆匆带着工人从大门口奔向了原料车间,人越聚越多了,大家瞠目结舌地看着。
看厂老头向厂长哭诉着:“厂长,多亏了他呀!把火拦住了,这厂子才保住呀。那火苗噌噌地……”
“那人呢?”
陈江河已经被火烤得灰头土脸,靠在已被烧黑的墙角下喘息着,墙皮被烧掉,裸露出了里面的砖石。陈江河突然发现了什么,慢慢爬上前。
离地一米多的高处墙砖上刻着不起眼的两个小人,一个大的牵着一个小的,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:骆玉珠和妈妈。看着那几个字,陈江河回想起玉珠曾对他说过:“我最幸福的时候,我们就住在那个袜厂旁边,每天天没亮,我妈就爬起来叫醒我,然后跟着她进车间,看她打扫卫生,烧水,等那些工人进来打开机器,一条条纱线交织在一起,一双双袜子眼睁睁地在眼前成形,太神奇了。”陈江河一动不动地趴在那,动情地回想着。
郑厂长激动地望着正在遐想的陈江河:“小伙子,你是我们袜厂的大恩人呐,救火英雄!谢谢您了。”
“你是我们厂里的家属吧。”
陈江河忙摇头。
“那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呢?你肯定是!”
陈江河忙一抹脸,土灰把脸抹得更花了。
郑厂长摆了摆手,对着厂老头说:“你先带他去洗一洗,再找身衣服给他换上。”
“厂长,我看你们厂在招工呢,我能不能试一下?”
郑厂长不由地愣了一下,重新审视了陈江河。这个年轻人知书达理,诚实厚道,更不用说刚正勇为,厂长甚是欢喜,他赞许地点了点头。
三
“拨浪—拨浪—破铜烂铁—鸡毛鸭毛鹅毛—换糖咯—”
淅淅沥沥的雨开始下起来,骆玉珠挑着换糖的担子急忙躲到杂货店的屋檐下,顺手抹了把额头,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。她仰头看了看灰蒙的天空,雨一时停不下来,就干脆坐下,从怀中拿出一块小麦饼啃起来,痴痴地想着什么。
过了一会,被大雨淋透的骆玉珠,拿起公用电话,眼中充满期待地听着。话筒中传来声音:“陈家村,找谁啊?”骆玉珠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,话筒那边喊起来:“喂?你找谁啊?说话!”骆玉珠一边抹着雨水和泪水,一边抱着话筒说不出话。
里面的人善意提醒:“姑娘,这是长途,很贵的。”
骆玉珠挂了电话,拿出钱递了过去。
就在骆玉珠挂了电话时,远处两个小商贩也跑到屋檐下避雨,冲骆玉珠笑了笑,好奇地打量。
“义乌的?我们是大陈村的,你呢?”
“就是陈家村隔壁的那个大陈村?中间隔了一座石桥?”骆玉珠点头笑了笑。
两人兴奋地说:“对对!你是陈家村出来的?”
骆玉珠摇摇头说:“我认识陈家村的巧姑……”
“哦,是陈金水的女儿,她和老公也一起出来了,跟她老公卖手套。她老公也是同村人,挺能干的,脑袋瓜子也挺活。”两人八卦似的侃了起来。
骆玉珠脸色苍白地回过头,望着天空越下越大的雨,回想着陈江河曾对她说:“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比做袜子还要赚钱的生意。猪皮手套,我们县里的猪皮快堆成山了……”想着往事,骆玉珠痛苦地摇了摇头,流着泪冲向雨中。
此时,高个子王大山正忧心忡忡地在扳道工屋里来回踱步,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稀饭和菜。窗外的雨渐渐大了起来,他扒着窗户往外眺望,空旷的路上仍不见玉珠人影。王大山架不住担心,还是披上雨衣走出了小木屋。
王大山冒着大雨赶到破棚找玉珠,推开门,里面空荡无人,已经湿成一片了。他神色焦急不安地转头望去,外面还是大雨如注,已经把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。
骆玉珠挑着担子被狂风暴雨裹挟着,边哭边走。
远处的王大山见此情景,没命地朝她跑了过来,一改以往憨厚的模样,利索地脱掉身上的雨衣,没等骆玉珠看明白,厚大的雨衣一下子将她裹住。
回到扳道工小屋,骆玉珠脸上出现了死灰色,她万念俱灰,裹紧被子坐在床头。王大山小心翼翼端来热水送到面前。
骆玉珠喝了一口热水,缓过气来后,轻声地请大山哥坐下。王大山拉过屋内仅有的一把椅子坐下,双手扶膝,一动不动地看着骆玉珠。
骆玉珠一抹嘴:“你成家了吗,大山哥?今年多大了?家里还有什么人?”王大山垂下头去又摇摇头:“我妈走了以后就我一个。”
骆玉珠默默注视着王大山,突然掀开被子蹭下床,凑近大个子向上瞧着他。王大山紧张地往后退缩。
“大山哥,你待人有情有义,我是无家可归,你把我娶了吧,从今往后,咱们俩搭帮过日子。”骆玉珠轻声说道,同时用力拉着王大山的双臂,“大山哥,娶我,不要彩礼,也不要你花钱。”
王大山抬起头不敢相信,又吃惊又迟疑地看着玉珠,他慢慢站起身,忍不住憨憨地笑了起来。骆玉珠也凄然一笑。
天上掉下个七仙女,地上冒出个田螺姑娘。好事来得就这么简单,一切顺理成章。小小巡道工小屋的小窗上,贴上了喜字和窗花,骆玉珠和王大山一人一边牵着红带子,新被子铺展在床上。摇曳着火苗的红蜡烛,将整个屋子映照得温暖红火。
骆玉珠难为情地看着王大山:“大山,今天我才有资格问,能不能……借我点钱,你老婆要做生意养家。”
喜气洋洋的王大山,眼巴巴地看着她。听了骆玉珠的话,王大山一脸苦笑,递上怀里准备好的存折:“早就想给你,这家都是你的。”
骆玉珠强调:“是借!我将来一定还你!”王大山拼命摆手。
王大山又拿出一个纸盒,打开一层又一层,取出一对银耳环:“这是我妈留下的。”
骆玉珠感动地看着王大山,轻声说:“给我戴上。”王大山笨手笨脚,始终戴不上。骆玉珠笑起来,自己接过将耳环戴到耳垂上,回头转向大山:“好不好看?”王大山点了点头,憨笑着。
烧开的水喷着热气,骆玉珠倒好一盆水,拉着王大山坐在床边,蹲下身体给王大山脱鞋袜。王大山要躲,骆玉珠用力地将他的脚按到盆中,撩拨着水给他洗脚,柔柔地说:“我是你老婆了,往后我伺候你。你出去踏踏实实地干活,我给你做饭,洗衣服,给你洗脚。”
王大山露出感动的目光,眼中闪现着泪花。
骆玉珠将洗脚水端出门,用力泼向黑暗,她抬头仰望星空,突然泪水不争气地淌落下来。她深深地吸了几口气,用手抹了把泪水,控制住情绪。一转身,看到王大山正站在门口,揪心地看着自己。
一天晚上,骆玉珠拿出新衣服,王大山无比惊诧地看着妻子,很听话地张开手臂问道:“你做的?”
骆玉珠一笑:“先试试合不合身,不合适再改。我前几天进城的时候看见布店在处理布料,就买了一些。”骆玉珠趴在高个子肩上,含笑注视着,“大山,我跟你商量个事。”
王大山一激动,转头紧张地看着骆玉珠。
骆玉珠拉着他并排坐下,柔声细语地说:“我看城里有好多废品,东西还挺好就不用了,我觉得这地方收破烂比鸡毛换糖强。以后我就给你做晚上一顿饭,多做点,剩下的第二天中午吃,这样行吧?”
王大山异样的眼光注视她,用力摇头。
骆玉珠皱眉说:“你不让我出去,我就没法挣钱了。”
王大山忙从口袋里拿出钱来,递到骆玉珠手里。
骆玉珠愣了愣,用感动的目光将钱塞了回去:“我已经有本钱了,你的钱你自己存着吧。我不是为了要你的钱才嫁给你的。”骆玉珠有些急,猛地站起身,钱一张张地飘落到地上。
王大山难过地低下头。
“我欠着人家的债呢,我得挣了钱还债!再说我还想用我赚的钱给你买衣服,买家里用的,给你做好吃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?”
“你是我媳妇,我的就是你的。”
骆玉珠慢慢蹲下身,捡起钱拉住王大山的手:“大山,这辈子我从不欠别人,包括我家里人。”
“你家里还有啥人?”
骆玉珠摇摇头,黯然神伤:“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,除了你。大山,我们说好,我以前的事你不用问,以后,我会真心守着你过一辈子。”
王大山翻了个身,迷糊地看着油灯下依然在缝补的妻子背影,撑起身把头凑到她的肩上。骆玉珠笑了笑,轻声说:“怎么又睡不踏实了,你一天要走多少路啊,这鞋也太费了。”大山从身后搂住她的腰:“几年前我妈给我买过一个媳妇,跑了。”
骆玉珠停住手,吃惊地听着。王大山轻声:“我怕你也跑了。”
骆玉珠凄然一笑,回头顺势将男人揽在怀里,像母亲对儿子一般轻抚他的脸庞,柔声道:“乖乖地睡吧,我不会跑的,因为碰上你是我的幸运。”王大山竟听话地闭上眼睛,一动不动躺在骆玉珠的怀中。骆玉珠抬起眼,看着摇曳的灯火,眼神变得无比宁静。

骆玉珠艰难地挑着货担,两脚一瘸一拐地沿着铁轨回家。她俯身揉了一下脚,这才发现货担里的废品掉了一路,她只得蹲下身子,一点点往回捡。实在累了,骆玉珠就随地坐下休息了一会,刚起身,就看到远远的一盏灯在黑暗中舞动,骆玉珠愣住了,想站起来,脚却钻心地疼。“哎!有人吗?”骆玉珠叫了一声。
灯光快速摇动着逼近,是王大山。
“你这么晚还没回去,我怕出事。越接越远就到这来了。”大山见骆玉珠走路一拐一拐的,急忙俯身抬起骆玉珠的脚,王大山倒吸一口冷气,连忙猫起身,示意骆玉珠趴在自己背上,骆玉珠不甘心地回头看了一眼货物:“大山,我的货。”
“放心,先把你背回去,回头我再来挑担,今天天色特别黑,不会有人的。”骆玉珠听话地趴在高个子的背上,一手搂着他的脖子,一手提着灯。灯光照亮了黑暗中的轨道,两人蹒跚着往前走。
四
陈江河暂时在袜厂装卸班安顿下来,每天和工友们用力将一包包货物装上运货车,一直送到大门口。陈江河向四处眺望,寻找着始终未出现的身影。当他坐在车间门口,看着机器吐出一双双袜子时,他的眼神是痴痴的。
一辆运货车驶进袜厂,车间的工人都出来诧异地看着。陈江河正在装袜子,听到郑厂长远远地喊。“都过来,卸货!”
“唉,又让人退回来,这月工资够呛了!”身边走过的工人摇头叹息着。
办公室里,郑厂长焦急地打着电话:“我们再改式样来不及嘛!你们变化也太快了,再说这几批货怎么办?如果你们不要,我们损失就大了!”
陈江河来到厂长室:“厂长!”郑厂长不耐烦地摆摆手。
郑厂长急得快哭出来:“老兄,帮帮忙吧!我这一厂子工资都发不出来了!”
陈江河守在门外,等郑厂长挂上电话,再次叫道。
郑厂长皱着眉问:“什么事?”
“厂长,上海那边退了我们三批货了,这袜子出什么问题了?”
郑厂长摇头:“人家嫌咱们式样老旧,跟不上形势。哎,跟你说也没用,赶紧帮着卸货去!”
陈江河没动窝,试探着说:“上海那地方不要,可能其他地方会要呢?我看我们厂经常有小贩偷着来进货。”
郑厂长没好气地说:“你说的我会想不到吗?那些小贩充其量摆个地摊,一天卖十几双。可咱这是几万双袜子,这么大的量,哪个地方吃得消啊,你没看咱们厂销售科的人全跑出去了?江河,踏实干好你的本职工作,别在这里添乱了!”
“厂长,让我试试,也许我行呢?”
郑厂长苦笑摇头:“陈江河啊,我知道年轻人有冲劲,刚来厂子立功心切,你要是能把退货都卖出去,我立刻把你提拔为销售科科长!”
陈江河欣喜地伸出双手,用力摇了摇郑厂长的手。
第二天一大早,陈江河在销售科给邱英杰打电话。邱英杰接到电话很兴奋:“江河,你去哪了?这些日子找不到你,真把我急死了!什么,袜子?”邱英杰神色严肃起来,朝传达室大爷轻声说:“您给我支笔。”邱英杰接过笔说,“你说袜厂的地址,联系电话。没问题,我马上通知冯大姐她们。曙光综合厂?厂名不带‘袜’字,哦,难怪别人找不到。”
陈江河听着话筒:“英杰哥,你帮我把消息传播出去,告诉所有集市上的人,就说这是骆玉珠当初进袜子的地方。好,我等你消息!”
销售科长老严眼巴巴地看着陈江河挂上电话,刚要上前。陈江河按住笑笑:“科长,我还得再打几个长途。”严科长只得点点头退回去等候。陈江河想了想,又拨通号码大声地说闽南话,连声调都变了:“阿兄,瓜西义乌的鸡毛。我这里有批式样非常好的销往上海的袜子,拉到你们那,保准一抢而空!虾米呀,福建这边,我第一时间告诉你的,虾米呀,抓牢机会!”
销售科长看着陈江河,听了他那不着边际的话大吃一惊,半张着嘴,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陈江河。
郑厂长焦急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踱步。销售科长快步走进厂长办公室:“厂长,你快去看看吧!那个陈江河……他……”
郑厂长吓了一跳,瞪着他:“陈江河怎么了?”
“他已经打了半天的长途了!全国各地都打遍了,而且用十几个地方的方言说话!”
郑厂长不相信地看着他。
销售科走廊内已经站满了人,人们都好奇地探头听着陈江河打电话。郑厂长跟着严科长急匆匆走来,就听到办公室里陈江河洪亮的声音,用纯熟的四川话推销:“你个瓜娃子,老子给你算笔账,从四川坐硬铺到杭州才花多少钱哈?老子不给你扯把子,我保证你带回的货,卖出的利润是车钱的几十倍!再说车站那哈有人接你不是?你过来个人,老子负责把货送上车嘛!”郑厂长停在门口,惊诧地看着陈江河挂上电话,尔后再次拨起。
有人小心翼翼地递上茶水,陈江河大大咧咧地喝了一口后,继续对着话筒用东北话:“婶啊,还记得我是谁不?我是义乌的鸡毛啊!咱叔身体还硬朗呗?……”
严科长不可思议地摇头,颤抖着说:“他到底是什么人啊,哪来的神仙?人脉那么广?”郑厂长也张大了嘴,呆呆地看着陈江河。
冯大姐已经搬到义乌新马路市场摆摊,她的周围聚集了一圈人,正听她又神秘又激动地透露商机:“我找到玉珠进袜子的地方了,让我也去进货呢!”
有人顿时兴奋起来:“真的?大姐,您在哪听到的?”
冯大姐忙嘘一下:“我带你们快点去拿货,别人还不知道呢!”
不远处邱英杰大声地朝商贩们说:“袜子大王进货的袜厂,想去的到我这里来报名。”一些摊主一听到玉珠进袜子的地方,都小跑过来,聚拢的人越来越多……
冯大姐等人默契地对视了一眼,也不顾自己的摊,撒腿就跑。冯大姐边跑边叫:“娟子,你替我看一下摊,我去买火车票!”
陈江河将最后一箱袜子帮冯大姐装上货车,邱英杰擦了把汗跳下车。冯大姐内心感慨地说:“真不知该怎样谢谢你,邱主任,帮我们找到生意,工商还帮我们来拉货!咱什么时候享受过这待遇啊—要是玉珠在就好了。”
见陈江河神色黯然,邱英杰将他拉到一边,轻声说:“你就准备在这等她?”
陈江河默默点头,心里说:“玉珠,对不住你了。我可把你的宝贝秘密撒播出去了。等你来当面骂我吧,我等着。”
“义乌那边我也帮你打听着,一有玉珠的消息我马上告诉你。江河,你不该猫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小厂里,好男儿志在四方,你这是何苦呢?”
陈江河凄然一笑:“英杰哥,玉珠的事拜托给你了。哥,你别劝我了,我倒开始喜欢这儿了。小小的袜厂大有文章可做,头些年我走的地方太多了,学的都是一个卖字,现在我要扎下根来,好好学学怎么做。我相信,如果没有经历过复杂商品的生产过程,就不能抓住义乌市场的未来。”
邱英杰吃惊地看着他,用赞赏的目光点了点头:“好啊,江河,你这话说得有水平,哥支持你!你将来会成为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儿!”邱英杰意味深长地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,“谢书记那天还问起你,我们需要你啊!自从第二代市场开业,现在从各地做小买卖的义乌人都开始回来了,慢慢形成了集聚效应,县里正在总结经验做好规划,想把小商品市场作为龙头,全力以赴发扬光大!”
陈江河苦笑:“英杰哥,几个月不见又有新词冒出来了,什么叫集聚效应?”
邱英杰比画着:“就好比美国的华尔街—金融中心,底特律—汽车制造中心。”
身后汽车启动。
“邱主任,走吗?”冯大姐问。
邱英杰遗憾地笑笑,有点不舍地看着陈江河:“只能下回跟你讲了,我得先把这些人跟货送回义乌去。”
陈江河也笑了:“英杰哥,每次见到你,我都感觉人活着特带劲。”
邱英杰走向货车,回头喊了一句:“江河,农民可以成为商人,义乌要实现几十万名农民身份的实质性变化,我们要创造‘农民商人’。梦想、创业、奋斗,人就得带劲地活着!”
陈江河深情地望着货车挥手。
“陈江河确实很有能力。不到半个月,退货和库存的几万双袜子,真被他卖光了!你说我能不把销售科长的位子给他吗?我一大厂长说话能不算数吗?”郑厂长苦口婆心地劝着垂头丧气的严科长。
严科长委屈地说:“那时他是一个装卸工,谁会知道有那么大本事啊。”
郑厂长背着手瞪他:“你的意思是不该给他当科长,该把我这个厂长的位置给他?”
严科长忙摆手:“厂长,我不是这意思!”
“厂长,您别做工作了!您分配我一个别的职位吧,我做不了销售科长。”陈江河站在门口。
郑厂长和严科长两人同时回过头去。
“那你想做什么?”
陈江河坦诚地说:“我想试试设计。”
两人诧异地交换了眼神,严科长:“江河,我们厂没有这部门啊,都是市场流行什么,我们做什么。”
陈江河一笑:“从我开始不就有了吗?郑厂长,科长,我觉得上海退货是个警示,以前我们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,统购统销。可现在市场搞活了,人的选择也多了,我们得把被动生产变成主动出击,我想学学设计新的花色品种!”
严科长带着嘲笑转头看郑厂长:“咱们厂生产袜子还要设计?不会让人笑掉了大牙吧?”
陈江河紧跟一句:“那我就做销售科长。”
严科长立刻笑起:“年轻人想法多,厂长,给他一个机会吧!”
陈江河憋住笑,看着严科长善变的脸。
邱英杰趴在传达室门口,微笑地听着电话里传来的牢骚声。“兄弟,这就是改革,如果没有障碍,没有陈旧的思想和禁锢,我们改它干什么?”邱英杰笑着说。
“所以我想走这条险路,英杰哥,你说我能走得通吗?”
邱英杰快活地笑起来:“走不通你再单干呗,又不会失去什么。你在体制外漂泊了那么多年。那个袜厂也许是老天特意安排给你的深造机会。兄弟,你是干大事的人,哥不会看错,奋勇前进,大胆地去实现梦想吧!”
陈江河动情地听着电话,长叹一声:“英杰哥,每次我想不开的时候,只要跟你通个电话,听着你说的梦想,我心里就特别舒畅。”
“江河,我有件事不理解,那个袜厂除了玉珠以前去那拿过货,对你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吗?你怎么会突然对做袜子那么感兴趣呢?”
陈江河笑了一下:“英杰哥,以后见面再说,不打扰你了,赶紧睡吧!”陈江河挂上电话,伸了个懒腰,忽然想起什么,摘下脖子上的玉坠,在灯下仔细地端详着……
“上海又把袜子全部退回来了,厂里的原料也不进了,大家都在疯传,厂子要倒闭!”陈江河走出设计室时,大学生小蒋告诉他说。陈江河走进车间,里面空无一人,工人们都茫然地坐在外面,议论着什么,看到陈江河和小蒋过来,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俩。
厂长的车驶进大门,停在办公楼前,他阴沉着脸下了车,众人无声地围上,陈江河也挤在人群中。郑厂长扫视了一下大家:“都先回家吧,大伙儿等消息。”
“厂长,我们不开工了?”
“我对不起大家,我们厂一直亏损,上级决定关闭袜厂,我也没有办法……”郑厂长嘴一咧拼命忍住泪水,深深地给工人们鞠了一躬。
“厂长,工资已经两个月没发了,家里还等着米下锅呢。”
“你有退路,我们怎么办?”工人们一片哀怨愁叹之声。
严科长推开设计室的门,坐到陈江河桌前。陈江河正写着什么。严科长带着哭腔:“江河,要是早听你的就好了。现在全完了!都赖我!产品推销不出去……”
陈江河没有抬头看他,窗外响起工人们的喊叫声。
“我们以厂为家,在这个厂子干了几十年,说垮就垮了!你们要给个说法,我们不回家!”
“败家子!败了就完了?去找上级领导,不然我们拿什么养家啊!”
陈江河将厚厚的十几页纸递到严科长面前。严科长诧异地看着陈江河:“这是什么?”
陈江河起身将图纸放到桌上:“严科长,你想办法帮我送到局领导那里,这是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做的承包方案。”
“承包?谁承包?”严科长吃惊得半张着嘴,注视着陈江河,“你早就料到袜厂要倒闭了?”
陈江河镇定自若地点头:“袜厂倒闭,我一点都不惊讶,我一直在等。老严,你还是很有能力的,如果你帮我,我可以提你当副厂长。我的方案是这样的,把库存分给大家抵部分工资,能卖多少卖多少,旧的机器设备转让出去,东厂区的土地可以出租。上面支持一点,我们再集一下资,准备进新的机器。”
老严不敢相信地摇头:“陈江河,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吧?”老严起身就要往外走。
陈江河把严科长堵在门口:“郑厂长有他的私心,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,他是想耗到调任别的厂时,再一走了之。”
老严怔怔地看着陈江河:“那你又凭什么接手?咱们一个国营厂,能让你一个合同工接手?你知道换一台机器要多少钱?陈江河,你也太自不量力了。”
“上级在提倡承包!你消息太不灵通了,杭州有好几家工厂都被承包了。我们厂承包不是不可能,只要有好的重组方案,领导一定会同意的。”陈江河自信地说,“东厂区的土地可以出租,甚至可以出卖!当然,这需要上级的批准。”
“你进新的机器就能保证新袜子卖得出去吗?”老严快要哭出声来了。
陈江河点头:“能,广州深圳那边已经开始流行,给我半年时间,全面转产玻璃袜!”
“玻璃袜?你竟然想到这个了?你为什么不早提,非要等厂子垮的这一天?”老严发蒙地看着陈江河,“陈江河,你到底是什么人啊……”
陈江河微微一笑,踌躇满志地深吸一口气,看向远处:“我是义乌人。”
五
骆玉珠一大早起来,收拾货摊准备出去时,胸部忽感一阵恶心,她捂上嘴拼命忍住。王大山偷偷打量着她,她又干呕起来,拼命起身冲出屋门,王大山忙跟到门外,轻拍骆玉珠的背,关切地问:“怎么不舒服,是不是病了?”
骆玉珠扶墙喘息着:“不知是不是吃那剩饭引起的?”
“玉珠,你身体不适,快回屋歇歇,我来收拾。”
骆玉珠点点头,被搀扶进屋:“吃点东西就老往上翻,不舒服。”
“今天你就不要出去了,我陪你去医院看看。”王大山说。
骆玉珠摇头:“不用,我吃点药就好。”
看着周围的人熙熙攘攘的,骆玉珠与王大山在医院门诊部的长椅上坐下。
“胃不舒服怎么还让你来妇科验尿呢?医生没说什么?”王大山百思不得其解。
骆玉珠看着眼前走过的一对对青年夫妇,仿佛察觉到了什么,心事重重地起身:“我去看看结果出来没?”
王大山忙起身:“我跟你去!”
骆玉珠摆手:“你坐这儿等着。”骆玉珠沿着走廊走去。
窗外传来吆喝声:“手套嘞,正宗的猪皮手套……”骆玉珠停住脚步,掉转头望去,巧姑正站在医院栅栏外的一辆三轮车上吆喝。骆玉珠呼吸变得急促起来,她什么也没有想,便快步朝门外走去。
骆玉珠走出门来,一眼就看到陈大光正趴在三轮车把上跟媳妇说笑:“你再大点声!”巧姑踹他一脚:“我再喊就上房揭瓦了!”
突然巧姑愣住,踹了踹陈大光,怔怔地看着眼前的骆玉珠。陈大光没察觉,还在笑:“别踹了,行不行?”陈大光看到媳妇的神色,抬头向医院大门看去,也惊呆了。
骆玉珠惊诧地打量两人,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“骆……骆玉珠!”
巧姑跳下三轮车问:“玉珠姐,你怎么在这?”
骆玉珠仿佛已经明白了什么,急切地拉住巧姑的手:“陈江河在哪?”
“那晚我跟大光跑了出来,鸡毛哥送行时,把他所有的钱都给了我,还让我们好好地做手套生意。鸡毛哥太好了,他说他不能跑,他要等你。玉珠姐,你没事吧?”巧姑担忧地看着恍惚的骆玉珠。
陈大光叹息:“我们都以为你跟鸡毛哥远走高飞了呢,后来碰到过村里的人,说鸡毛哥也跟巧姑他爹闹翻了,为了找你,好端端的干部不做,现成的钱也不赚,也不知道去了哪。”
骆玉珠已经明白,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。她万念俱灰,一动不动,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。
巧姑摇着玉珠的手臂:“玉珠姐,你说句话啊,你现在什么情况?跟鸡毛哥在一起吗?”
陈大光像是看见了什么:“工商来了,快走!”巧姑忙跳上车,陈大光用力蹬起三轮车。
“玉珠姐,你去找鸡毛哥吧!他为了你,跟我爸都闹翻了,他肯定一根筋地在苦苦等你!”巧姑回头喊道。
骆玉珠像塑像一般站着,泪水终于从眼眶中涌出,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到:“等我?”
王大山不安地坐在长椅上等着,突然听到走廊尽头护士在喊:“骆玉珠,拿结果!”
王大山忙起身跑去:“哎,来了!”他挤过人群,凑到窗台前赔着笑,“骆玉珠,医生,我是她丈夫,您给我就行。”
化验单递出,王大山急切地看着,却摸不着头脑。轻声嘀咕:“阳性?阳性什么意思?”
旁边的人笑道:“你老婆怀上了!”
王大山惊呆,露出不敢相信的神色。
“玉珠,玉珠,我们有孩子了!”身后传来王大山的叫喊声,骆玉珠毫无察觉,她被扑上前的王大山扳过身子,用力地搂进怀里。王大山由于激动,含泪哽咽着:“你怀上了,我们有孩子了!”
骆玉珠趴在大个子的肩上,酸甜苦辣咸,五味杂陈,泪如雨下。

![【学习强国】[挑战答题]带选项完整题库(2020年4月20日更新)-武穆逸仙](https://www.iwmyx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timg-300x200.jpg)


![【学习强国】[新闻采编学习(记者证)]带选项完整题库(2019年11月1日更新)-武穆逸仙](https://www.iwmyx.cn/wp-content/uploads/2019/12/77ed36f4b18679ce54d4cebda306117e-300x200.jpg)